
随着抖音被国营的央视入股1%,快手被国营的北京电视台入股1%,短视频直播赛道公私合营开始了(2022年11月便传出消息,且被天眼查数据石锤证实)。“特殊管理股”已在短视频平台悄然落地,尽管国有资本仅占1%的股份,却拥有相对较大的决策权力,甚至是一票否决权。这种特殊的“1%股份一票否决权”安排不禁让人思考:这种国有资本与私有资本的混合形态,与我们理解的现代商业文明相距多远? 现代国家的伟大理想,需要一个健康、活跃的现代商业文明作为支撑。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如果脱离了实事求是,忽视了经济基础的健康发展,那么其任何宏伟的社会理想都可能沦为泡影,都终将成为遥不可及的“梦”。
而当前,我们正面临着经济下行风险、创新乏力等严峻问题,民营企业纷纷“用脚投票”,这些都预示着潜在的经济危机。也许2024年,或者即将到来的某一年,大饥荒、大萧条和社会大动荡会接踵而来,未来三十年大萧条绝不是危言耸听。在这种情况下,国有资本到底应该如何做?这直接决定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政府担心抖音、快手等公司坐拥庞大社会流量,进而对统一的宣传口径造成威胁。当然,政府凭借“特殊管理股”介入企业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社会稳定和宣传口径的一致性,但过度的干预可能会破坏市场机制,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 现代商业文明社会是一套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包括企业、企业家、市场、政府、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在内的所有参与要素各司其职,进而形成了市场和商业文明的基本原则。不能说你入了股就怎么样,一切都要遵循经济发展和市场运作规律,要服务于“效率、信用、公平”原则。 以1%的股份拥有一票否决权,这是否意味着国有资本或政府将直接承担企业的创新和发展责任?如果国有资本以监管者的身份频繁介入企业管理,岂不是在替企业家做决策,甚至可能形成对企业创新的无形束缚?无疑,公有资本代替管理机构介入企业管理将会扼杀企业的创新精神和发展动力。而且政府本身已经通过一系列的管理机构来监督市场、规范企业行为,再“另辟蹊径”介入到私营企业管理之中,岂不是浪费公共资源、自己打自己脸。

倘若此种做法不受约束,必将造成严重的影响和后果。估计下一步所有带有流量传播属性的企业都要受“1%股份一票否决权”蹂躏,再继续推而广之,各级政府甚至会进行效仿渗入所有民营企业之中,50年代的公私合营又将卷土重来。这样一来,“管”是“管”好了,但在政府不可避免的过度干预下,必然进一步恶化营商环境,抑制私营企业创新和发展活力,影响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届时,这种“公私合营”该如何承担税收、就业和创新责任,提振市场信心,以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崩溃? 有人想用马云的例子来为政府和国资介入的“特殊管理股”开脱。马云在阿里巴巴的股权被稀释后,依然保留着一票否决权,但这是对其创始人地位和对公司愿景的一种保护。然而,如果一个外来股东,仅凭1%的股份就可以对企业管理和决策做出决定性干预,这种情况与马云的情形截然不同。这不仅可能扭曲企业的决策过程,也可能抑制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市场活力。抖音、快手们之所以别无选择,不是因为国资和政府是它们的“马云”,更多只是迫于威权所表现出的无奈之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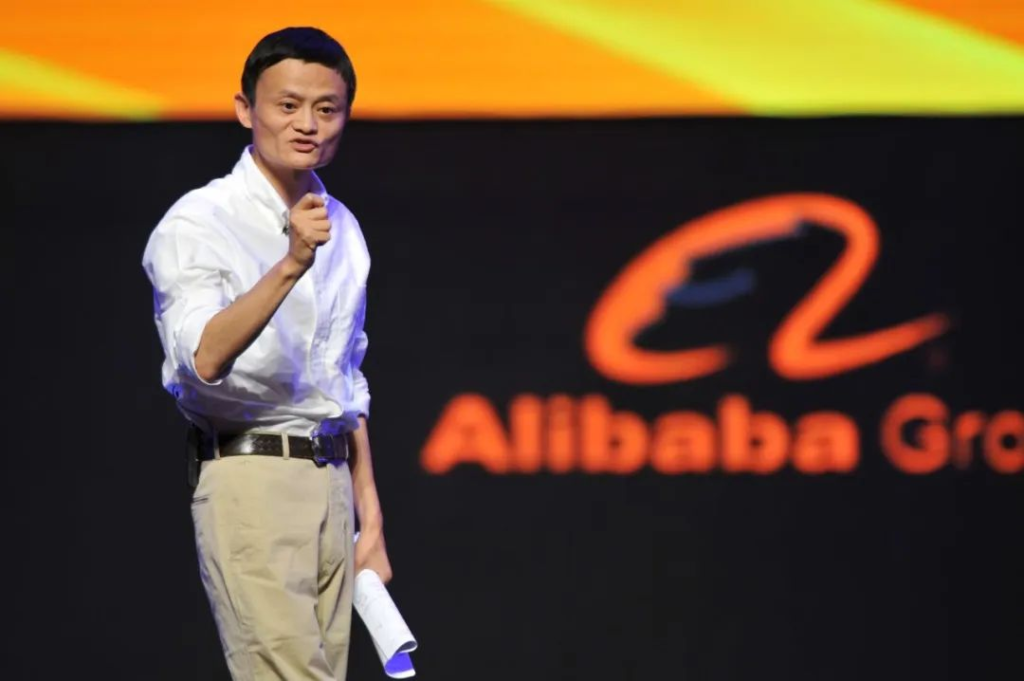
“特殊管理股”的做法表明,我们依然陷入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二元分化误区之中,错误地认为公有资本比私有资本高人一等,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高人一等,甚至依旧沉溺于全能政府统管一切的幻想和自嗨之中。悉知公有制和私有制是统一于共有制,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是平等互补的关系,它们共同为市场经济活力贡献资本力量。 而从“效率、信用、公平”原则来看,传统意义上的国企本就不应该存在。政府和企业应该是各取所长、各司其职的合作关系,政府并不亲自下场去创办和管理企业,而是通过公有资本参与到企业投资之中,不是要介入到企业管理和决策之中,而是以实现公有资本收益,促进市场经济和产业发展为目标。 公有资本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发现并发挥了公有资本的真正价值,这也是中国模式的精髓所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无法解释前面几十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虽然从理想的共有制运作模式(即20%的公有资本+80%的私有资本)来看,我们还有学习和改进空间,但改革开放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发挥了公有资本的社会兜底作用,公有资本在众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战略性行业的发展和扶贫减贫等方面。
而且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优秀民营企业和私有资本,大多来源于八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尤其是国企改私,继而才有了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大繁荣。今天仍有不少“专家”耿耿于怀于当时的“国有资产流失”,但回过头来看,当初的做法完全可以看作共有资本的一种投资方式,其最终收益是数十年经济辉煌发展这个最大的“蛋糕”。

公有资本当然可以投资入股民营企业,广大受“融资难、融资贵”困扰的民营企业也欢迎拥有雄厚资金底蕴和信用背书的公有资本来投资,以解燃眉之急。按照共有制理论,公有资本应该无差异介入到各行各业的投资之中,一方面可以适当的起到监督职责,另一方面还可以为企业和产业孵化提供优质充足的资金,此外还可以籍此获得投资回报实现公有资本增值,缓解政府财政赤字,为社会兜底服务提供可持续的资金保障。问题的关键在于参与的方式和程度,当介入逾越了合理的边界,变成对企业决策的直接干预时,问题就出现了。 理想的状态是,公有资本应以正常投资者的身份出现,既能够监督企业的健康发展,又不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和创新活动。从资本角度,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运作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社会生态构建不仅仅是由权力来编织,不是公有资本说的算,私有资本也要贡献很大力量。 公有资本的角色不应该是一个独裁者或绝对的控制者。相反,它应该是一个合作伙伴,一个促进者,帮助私营企业发展壮大,同时保护消费者和员工的权益。公有资本的干预应当是透明和合理的,以确保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而且合作必须建立在互相尊重和平等合作的基础上,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方面控制。

在公有资本运作上,我们应该学习新加坡的淡马锡国有资本管理模式,也应该学习国内现成的已被事实验证过的“合肥模式”。 淡马锡模式的精髓是“以管资本而非管资产方式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最大限度地奉行市场化和企业化经营思想和模式,用再商言商、管理企业而不是管理政府部门的指导思想经营企业”。此种模式造就了世界上最成功的“国企”和最优秀的主权投资基金,为新加坡从蕞尔小国崛起为高度发达的现代商业文明国家和高福利社会提供了坚实保障。 而合肥市则以政府“风投”闻名于世,在短短十余年间,发挥国有资本的引头作用,用“以投带引”的合肥模式,撬动了中国显示屏产业、半导体产业和新能源汽车的半壁江山,一举跨入万亿GDP俱乐部,实现了十年“换道超车”,从中部落寞省会城市跻身“新一线”城市行列,成为城市发展新标杆。 合肥政府以投资的方式引入企业,然后在适当时期退出,资金回收后继续投资引入新的企业,这是典型的风险投资策略。有时即便是作为大股东入股,合肥政府依然把决策和管理权留给企业,从来没有“1%股份一票否决权”的“强盗逻辑”想法。正是这样的魄力和远见,让合肥成为企业家和创新企业向往的创业投资热土,也为合肥市政府赢得各方美誉,相比之下,动“特殊管理股”歪心思之众是该自行羞愧、扪心自问了!
其它文章
文明奇点:川马解构民主制度(下篇 – 2)
文明奇点:川马解构民主制度(下篇 – 1)
文明奇点:马斯克开启智能文明社会治理新纪元(上篇)
解开滞涨之结:哈耶克可以兼容凯恩斯
认清三害
永不枯竭的诺奖:公有资本的操盘标杆
支招武大郎,守护金莲,不进西门
经济发展和权力构建的第一定律:产权的界定和保护
民企可以欢迎国有资本入股,但如何注意吃相
1%股有一票否决权,离现代商业文明有多远
刀郎新歌的商业逻辑
作业
人生导师
纪念父亲
- 文明奇点:川马解构民主制度(下篇 – 2) - 03/21/25
- 文明奇点:川马解构民主制度(下篇 – 1) - 03/20/25
- 文明奇点:马斯克开启智能文明社会治理新纪元(上篇) - 03/18/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