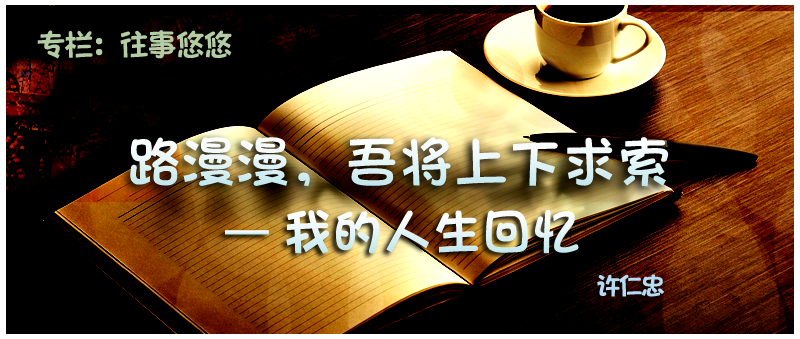
第一篇 三人行,必有吾师焉 — 我的学习生活
如果说我这七十多年是过得比较欢愉比较坦途比较有成就感比较感觉良好的话,从幼年开始各个阶段的学习,以及一直坚持的边学边做,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终身学习终身教育”是所有这一切的基础和保障。
我把我的学习生活,分为这么几个阶段来记忆:幼年与小学学习;中学学习,刻意的把它分成初中和高中;大学前工作阶段的学习;改变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大学学习;在高校任教第一个八年的学习;商海无涯中的学习;退休前十年在高校的再学习;民办高校教学与管理中的学习。
(一)幼年与小学的学习
小学和幼儿园阶段的学习总的来说是懵懂萌矇的,特别是小学五年级之前的所有,记忆中似有似无似多似少似深似浅极不清晰。
我记不清楚自己读过幼稚园没有?我们那个年代似乎没有幼儿园,但记忆中又总是觉得好像有过,总觉得似乎读过,脑海中总有一种在幼稚园学习的印象和感觉。
小学的第一阶段是在城中心的陕西街小学读的,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它应该是当时的“重点小学”。记忆中很深刻的是校园,虽然是城中老式的平房建筑,但给人感觉很宽很大,教室很多操场也特别大,操场前边有一个主席台,供各种活动使用, 长大甚至成年后,都有数次在梦中“回忆”到那个校园,可见其印象之深。
学业如何没有什么记忆,有一件事是我记忆特别深刻的,这件事至少说明当时在班主任老师的心目中,我是属于好学生乖娃娃之类的!这件事想起来也特别奇怪,大约是小学二年级或三年级吧,班主任潘老师有一天让我去邮局替她寄一封信,为了放心她又让班上一位姓郑的女同学跟着我。邮局在很繁华的东御街,我懵懵懂懂的居然走到东御街上的一家银行中去了,那位姓郑的女同学似乎比我更聪明更醒事了解的事更多,她叫住了我说走错了,她说这是银行,银行和邮局是两回事,说老实话,我之所以走进去,其实是真的不知道银行和邮局是两回事,概念上我是把它们二者混为一体了,所以这位郑姓女同学给我上了银行和邮局不是一家的启蒙课。
这几年幼时的懵懂学习,还要特别提到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安徽人,应该家境不差吧,因为他在来四川逃难前在安徽读过书,文化程度应该至少是高小吧,也许还要高一点,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安徽逃难到了四川。父亲有一定文化对我影响应该是较深的,虽然他从来未曾指导过我的学习,但在幼时让我产生了对文化当然也包括对知识的崇敬和向往。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是父亲好像在当时解放初期的报纸上发表过小方块文章,很小的一块豆腐干文章,他特意把文章指给我看,看到文章末尾他的署名,一种对文化的崇拜油然而生。
如果说父亲虽然没有对我的学习有过具体的指导,但在某些方面的带给我良好学习习惯使我受益匪浅 ,比如阅读书籍,十岁左右时他常带我到市中区的工人文化宫去逛,但实际上在里边是看书,一本当年书名叫《红旗飘飘》的短篇回忆文章书,就是在文化宫反反复复多次阅读的,另外还有一部书名叫《保卫延安》的长篇小说也读了多次。应当说这些阅读对我后来汉语言的学习和提高是很有补益的。再就是每个周末,他会让我到他工作的商店附近的一家叫智育电影院的去看一场电影,这家智育电影院在春熙路一带,好像是现在的王府井的位置,它不放新电影片只放旧片所以票价较低。每周一次的这种观影活动,对我后来眼界的逐步宽阔逐步的认识外部世界也是很有补益的。
亲眼看到母亲的一件事也使我对知识产生无比的崇敬和向往。母亲那时在四川大学消费合作社工作,应是三、四年级吧,我几乎每周末都要从住在城中的光华街,走路到城郊四川大学去,那里除有我工作的母亲之外,还有我的一个兄弟和妹妹。有一次到了四川大学,母亲的同事告诉我可以到哲学楼去找到她,于是我便前往哲学楼去找她。到了哲学楼,母亲在大门口静坐着,好像没有什么事,面前放着两个较大的木盒子,里边盛着一些要出售的点心。后来得知是当年的四川大学研究生招生考试在哲学楼内进行,母亲那种呆坐式的服务使我对高层次教育和文化的敬仰和惧怕油然而生,这种敬仰和惧怕是由母亲的低层次服务与教室内高层次学生的被服务的巨大落差导致的。
还要说到的一件事就是每周由城中的光华街去四川大学,最短的路径是由光华街到状元街再到东丁字街,走到当初的锦江边也就是今天的锦江大桥。坐渡船过锦江就到了华西埧也就是当年四川医学院,然后再穿过四川音乐学院及成都工学院到四川大学。不过这条最短的路径当年很少走,因为那时锦江上还没有桥,要渡过锦江需要给摆渡人交一分钱的船钱,这对当时的我来讲恐怕是个天文数字,至少是极舍不得。更多的时候是到了锦江边后,就沿着向东的城墙走,走到现在的新南门处后转而向南仍然沿着城墙走到九眼桥,在那里有九眼桥了可以跨过锦江到四川大学。城墙就是当年的护城墙,其实墙下没有路,或者是有路而儿时的我不得而知,都是在城墙上顺着人踏出来的小路前行的,所以最初几次在不熟悉路径的时候是需要辩识方向和探路的,对一个十岁左右的孩提,方向的确认似乎难了点,但成功后的喜悦无疑对后来我学习平面几何产生了一种喜好和引导。
对小学学习稍有记忆的是1958年转学到了四川大学附属小学读五年级,这所小学现在叫劳动路小学,好像同时也叫四川大学附属小学。
在这所小学中学习了两年,体验中最深刻的是认识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以及他们的教授家庭。这一点应该是在我的心灵中有所触动,又使我对知识有了一种懵懂的崇拜和向往!这批四川大学与成都工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四川医学院等高校的高级知识分子子女的同学,我在日常的接触中,无论是言谈还是做事,都感到她们比我懂得多强得多,特别是在知识方面知道的东西比我多得多。后来到了几个同学的家中去,进入了他们家中的书房,满屋的书架和书籍使我对书籍其实是对知识无比景仰和崇敬!
在四川大学附属小学的这两年,还有一件事也对我学习知识有强烈向往萌动。不知道什么因缘,认识了四川大学图书馆的一位长辈老师,他居然数次带我去了四川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室。一排排的高大的书架,耸立在我眼前,使我震惊使我惧怕但更使我向往。
应该说我还是有点读书的天分的,虽然一直自我感觉同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同学差距很大,比不上他们,但在事实上的学习中,我和他们在学习上的交流很通畅,在有些时候我明显的感觉到,他们对我有所赞许有所赞扬,感觉到他们也很愿意同我进行学习知识上的交流。这批高级知识分子子女的同学,在我们小学毕业后与他们分道扬镳了。三年后,当我进入成都七中读高中时,再次相逢又成为了高中同学。
1958年在共和国历史上,是一个值得书写的年代。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后,这一年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鼓舞下,一切都很亢奋都很热烈都很鼓舞人心!在“超英赶美”的年代中,小学生们也积极参与了大炼钢铁等群众活动。记忆中一个“英雄赶派克”的活报剧。在小学生涯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四川大学附属小学读书的这两年中,一个意外的学习收获就是接触了厨艺。当年我的母亲是不管我们的,作为“半边天”她很投入工作,几乎是每个月回来一次放下十元钱作为我和我的兄弟的生活费便难见人影,而当年父亲因为一些政治因素被下放到了远在青白江的成都钢铁厂工作。我的小妹寄托在一位范姓家庭中,我们称为范爸爸的是川大红瓦村食堂的一位炊事员,由于这个原因,我得以经常在红瓦村食堂的厨房内玩耍,从而认识了很多炊事员长辈。除了耳闻目睹他们做饭做菜外,更身体力行的参加到白案师傅做馒头花卷的工作中:供应给大学生吃的馒头花卷,因为数量太多太大,都是头天下午七八点钟开始做的,五六个师傅一直要做到深夜十二点甚至凌晨一两点。我放学晚饭后即加入他们的工作,具体事情是的把他们做好的花卷或者切好的馒头放入大蒸笼内,这种参与让我懂得了馒头是怎样由面粉做成的。当然,这种参与也让我从小就对做菜做饭这种事情有一种兴趣和耐心。
1957年的反右斗争肯定会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感觉乃至恐惧,这些感觉与恐惧中,比较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当时的所谓川大的大右派冯元春,我在57年去川大时曾看见她被批斗的情况,怎么也想象不到一位很年轻的女大学生,居然是极右学生大右派,批斗会的声势和吼声使我有一种莫名的惧怕。再就是我的父亲,在57年的某天夜晚,被人押着回家来取洗涮用品和换洗衣服,朦朦胧胧的说是犯了错误,需要封闭着学习改造,不管怎样父亲这样被押着回家,对一个十岁的孩子还是会产生极度恐惧心的。
就这样,懵懵懂懂的不优秀但也不后进的渡过了小学六年,在困难年代的1960年进入了中学。
(未完待续)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前言)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0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2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70)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八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七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六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五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四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三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二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一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九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八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七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六篇)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致读者)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五篇)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30)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四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三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二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一篇)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7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后记(317)
许仁忠: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我的市场经济面面观(316)
许仁忠: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我的市场经济面面观(315)
许仁忠: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我的市场经济面面观(314)
许仁忠: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我的市场经济面面观(313)
许仁忠: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我的市场经济面面观(312)
许仁忠: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我的市场经济面面观(311)
许仁忠: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我的市场经济面面观(310)
许仁忠: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我的市场经济面面观(30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41)
许仁忠: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我的市场经济面面观(308)
许仁忠: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我的市场经济面面观(307)
许仁忠: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我的市场经济面面观(30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30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30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30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30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30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30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9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9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9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9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9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9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9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9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9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9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2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9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4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9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7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7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7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7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7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7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7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7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7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7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7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6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6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5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8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1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5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5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4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4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4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4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4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4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教育观念(24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2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教育观念(24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教育观念(24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教育观念(24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教育观念(23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教育观念(23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3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3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3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3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3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3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3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3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2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2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2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2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25)
-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前言) - 01/28/25
- 欧州旅游:中东欧(三) - 01/27/25
-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02) - 01/26/25







今天刚刚发现这个地方。 标注一下慢慢读。
欢迎光临。
慢慢看,内容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