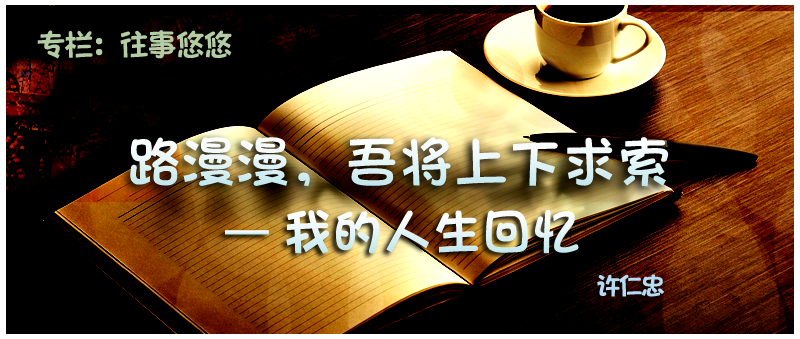
(续)第十四篇 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我的“城南纪事”
其实从综合的情况来看,成都的拆迁总体是做的比较好的,一直提出的口号就是“阳光拆迁”,应该说从大的方面确实是这样的,政策呀程序呀各个拆迁环节都会公示,表现出相当的公开公正阳光度。但在具体的拆迁操作上还是有不少使人疑虑的地方,比如具体负责拆迁的机构和人员,对外讲都是政府部门的这个拆迁项目的工作人员,如果不仔细观察和了解会真认为是如此,但通过接触沟通交流后就发现他们是接受了这个项目拆迁任务的一个机构,具体的拆迁由他们全面负责但他们不是政府工作人员。除了交流言谈中表现出来外,关键是在拆迁补偿上金额的讨论使人觉得可操作性很大,这些机构和人员在不同沟通交流阶段说到的拆迁补偿金额差异还是很大。
当我对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提出的拆迁补偿金额提出异议的时候,他们一方面对我提出的问题进行解释,但另一方面又表示可以尽量的向领导争取提高补偿金额,而且几乎就是在同时,根据我提出房屋的现状与补偿金额不很符合的地方,他们庚即进行了修正把补偿金额提高到了70多万,与第一次的拆迁补偿金额相差将近10万。当然后来又进行了多次沟通交流,我当然每次都会提出一些新问题请他们研究和回答,随着每一次的讨论补偿金额都会有所提高,从70多万逐渐到80多万最后上了90万,说内心话和真心话我自己对这种变化都感到很惊诧,心里边老是在嘀咕第一次那个60多万是根据什么标准计算出来的呢?
当双方讨论到拆迁补偿上了90万之后局面就有点胶着起来,这时我也感觉到可能这个金额比较接近他们的上限了,所以我也不着急与他们进行沟通交流,他们来找了我几次我虽然没有很明确的提出要求但都让他们感觉到对拆迁补偿金额我们还是不是很满意,这样使得在每次交流中他们都比较主动的找到一些可以增加一点补偿金额的理由一两万两三万的增加了一些金额。如果过分贪婪一些本来还是可以在熬熬价,但这时他们也通过我母亲的单位管退休人员的机构与我联系了一下,考虑到方方面面的综合因素,我最终也在拆迁补偿金额谈成97万时同意签订拆迁合同,这个金额相比起第一次提出的金额相差了足足30万。
也正是这个长达一两个月的拆迁补偿金额的讨论磋商过程,特别是过程中金额的不断变动使我感到政府负责拆迁项目的机构是把拆迁工作外包出去了的,具体负责拆迁工作操作的是个有利益收入的机构,因为具体每次沟通交流的过程中都有很多比较有趣的细节,这些细节很明显的表现出来这个有利益收入的机构和人员的想法和做法。在沟通交流过程中他们大概有四五个人参与,好像负主要责任的是其中的两三个人,各种原因,我们每次的沟通交流纷围都是比较好的,不考虑双方利益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朋友,他们这些人中也表现出来各方面的差异,比如性格啦言谈啦等等,看得出来他们对我的感觉也是比较好的。最为有趣的是一切尘埃落地之后又过了一年多,这些拆迁工作人员中的一个人居然应聘到我担任院长的四川天一学院的外包交通车队担任驾驶员,这个人就是我拆迁当时觉得性格和言谈都比较更好一点的人,他在与我的摆谈交流中说到当初拆迁的事情时印证了我对拆迁机构的分析和判断。
第二个拆迁是在现在的成都东站附近,1992年成都市第一个开发的市场就是它,大家通常叫他西部市场。当年这个市场是按照5万元一套售出的,大约有40个平方,一楼一底两层,底层是营业用房,楼上是住宿或者办公用房均可,带有卫生间上下水也很健全,应该说品质和性价比都不错。比较遗憾的是当年一轰而上成都市就东南西北四面开花建了很多类似的市场,西部市场虽然是首创的第一家,但也没有逃脱形不成真正市场的厄运,房子建成交付后市场一直没有真正形成,放在那里一放就是十多年,前几年根本没有办法租出去使用,后来有一些做加工业的人租来使用但租金很低,我那套房后来就租给一个做切面的人在使用。
十多年过去了市场所占用的那块土地因为成都东站的逐渐形成要拆迁使用了,于是我又一次面临着拆迁补偿谈判。操作拆迁的工作人员一见面,我就感觉到和第一次拆迁的情况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一次的情况应该说是比较简单透明一些,因为当时市场所建而现在要拆迁的房子都是那种户型和格式,只是每户之间略有点面积差异而已,所以是比较透明的公布了一个拆迁补偿计算方法,如果没有后来表现出来的一个异常问题出现,拆迁应该是不麻烦比较顺利的。出现了个什么异常情况呢?就是当时成都东站那一片开发已比较好了,在被拆迁房屋的估价上拆迁方和被拆迁方有差异和矛盾,就是被拆迁方内部在看法上差异也很大,这样就形成了被拆迁方中多数人因为补偿金额问题而拒绝签订拆迁合同,当然房子也迟迟不能拆迁。
在这种状态和背景下,拆迁方工作人员中就有了一些不太好的作法,也许是为了尽快的完成拆迁任务而过于急迫,一些不太好的手段他们也开始使用,当时市场被拆迁户中盛传不少人受到威胁,也好像似乎有一两户拆迁合同还没有签就被破门而入了,这样使得双方矛盾更大被拆迁户们也开始相互串联团结起来拒绝拆迁。我其实一开始就对拆迁补偿没有多大的意见,因为政策是公开透明的,我想这应该是政府的意见,其实当初5万元买的房子计算下来的赔偿款将近70万,应该是很不错的了,但因为被拆迁方大家在串联号召团结,去签了拆迁合同的人很少,并且其中多数都是外地人,成都市本地的人基本没有去莶,为了不拂众意我也就成了观望派。
其实我明白最终这个拆迁合同还是要签的,不是我一个人其实大家最终都只有去莶,除非你是坚决的要当钉子户拒绝拆迁。因为这个拆迁补偿的政策是政府相关部门出台的,与这些具体执行和操作拆迁的工作人员无关,如果嫌补偿金额低了需要找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和协调,这在当时应该是一件不太好办的事,但既然大家都没有去签合同,我自然也没有去搭理这些拆迁工作人员。这种双方僵持着的局面使拆迁操作机构的工作人员十分着急,所以凡是能够使用的方法和手段他们都用上了,我就遇到了很搞笑的一幕。
那段时间中双方主要是电话联系,很多时候电话通了之后我都找一些理由来推脱,也许是他们万般无奈有一天就上门来了。他们在门外敲门我明确识别到他们是拆迁方工作人员后,也打开了门但没有让他们进入房中。就在门口我与他们交谈,他们来的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女孩还比较年轻,因为一直以来沟通的氛围都比较好,所以虽然是站在门口谈事情气氛也还是很不错,我也如实相告我对赔偿金额没有多大意见,只是现在多数被拆迁户都没有去签合同所以我也想等等看看,至少和大家统一步伐,我还开玩笑的告诉他们如果今后签合同的人多了,让他们直接通知我,那时我也会去签的。
正在气氛很好的交流之中,突然从门道侧边一个隐藏之处幽灵般的闪出来一个戴着墨色眼镜的人,一言不发的矗立在他们两人背后,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他好像是黑社会的打手,这种局面一出现我立马就很不高兴了,我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先来的一男一女急忙解释这是他们的驾驶员,后进来的那个人也赶忙把墨色眼镜取了,起眼一看应该是一个不很懂事的年轻人。我很严肃的告诉他们,我是西南财经大学的教授,知理懂法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不会被这种手段和伎俩所吓到的,本来已经说好如果签合同的人比较多了他们通知我,我就会到他们拆迁办公室去莶合同的,既然现在出现了这种使人不愉快的现象,我就告诉他们签合的时候地方要改一改,到时候让他们到西南财经大学温江柳林校区我上课的地方我上课的那一天来找我签合同。
后来整个拆迁进程发展的也快,因为政府相关部门确定的大政策轻易是不会有所改变的,加之5万投入得到70万左右的补偿本来也很不错了,并且政府的拆迁资金很到位,几乎是在签拆迁合同的当天就能打款第二天就能到账,所以被撤迁户们逐渐在明白事理之后也就先先后后陆陆续续的去莶了拆迁合同。我这边因为有之前那戏剧性的一幕,最后他们真的是开着车到温江我上课那一天在西南财经大学柳林校区等到我下课后才签的合同。这几位工作人员可能文化程度也比较低,他们之前还真没有到大学里边逛过,这次因为要在教学楼等着我签合同,还真领略了一下大学的校园风光和先生们上课的情景,合同签完之后他们颇有点感触的说,许老师给了我们一次到大学参观学习的机会。
(未完待续)
我的更多文章: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前言)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0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2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70)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八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七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六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五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四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三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二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一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九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八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七篇)
-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前言) - 01/28/25
- 欧州旅游:中东欧(三) - 01/27/25
-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02) - 01/2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