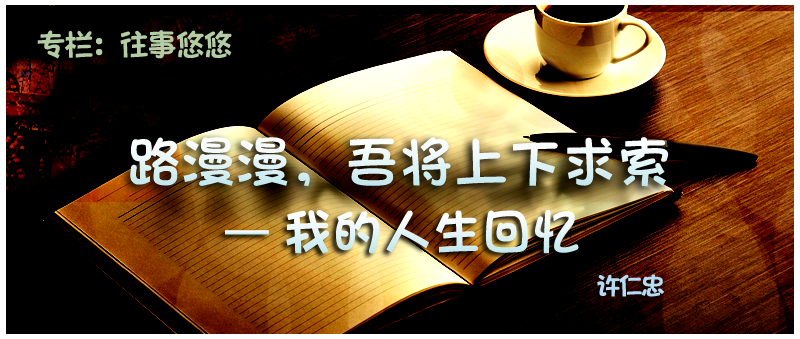
(续)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
从1972年初起我便到了金牛区商业局工作,先是借调了一年多,后来便以工代干转成了金牛区商业局的正式干部,具体的工作岗位是金牛区商业局办公室,到1978年9月我考入成都工学院读大学,我在这里工作了七年多。之所以仅在基层的石羊供销社工作了一年多年便被调到了金牛区商业局,我这个老三届高66级的学历特别是在成都七中读书时所锻炼出来的文字能力起到了至关重大的作用,真正的高三毕业生学历与能力,在当时的金牛区商业局包括整个金牛区都是很引人注目的,所以我在金牛区商业局的七年多中,事实上成了金牛区商业系统乃至财贸系统的秀才。
几年的秀才生涯其实是无奈和无聊的,潜意识深处家中有些事情我必须在也只能在这里完成,使得即便是无聊与无奈,我还得费尽心思的在这里起到恰如其分的作用,好在最终家中的事也修成正果,在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的1966年,我终于虽然是很费劲但也是比较顺利的把在乡下呆了五六年的兄弟调回了成都工作,让赖在成都没有下乡的妹妹合法的办了免下乡手续。当然这种秀才生涯也让我近距离观察到当年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经济上的计划经济机制的毛病和弊端。
计划经济机制在当年可以说已经在特殊的政治氛围中被发挥到极致,这个机制已经很成熟了,成熟到无论哪个方面的人们都知道与自己相关的经济行为都要受到计划的约束,所以人们基本没有把事情做好的愿望和动力,一切都有计划按计划执行就行了,当然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经济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每况愈下的生产力让物资一天比一天匮乏,人们生活中的绝大多数物资都要凭票定量供应,票证本身就是一种计划,票证发到老百姓手中后商业部门就得竭尽全力的组织商品保证票证要供应商品的兑现,这在当时实际上是很吃力很困难的一件事。我在前边我的工作生涯中很详细记录的两件事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整体的经济状况已经被计划经济带到歧路和尽头的事实。
一件事情是当年所谓的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的供应,一个有几十万人口的金牛区,每个季度分配到来的自行车和缝纫机数量之少让人震惊,少到什么程度呢?少到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敢去接手这些自行车缝纫机的分配,谁去过问谁去问津那就是惹火烧身,所以这件事情居然最后是由我这个没有任何职务的商业局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来承担和解决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区委区政府因为工作还是需要一些高档烟酒,这个在今天看来十分简单的问题在当年还得让区委分管财贸的副书记在成都市财贸工作会议上提出才能得到解决,更为奇怪的是问题解决了由哪个渠道负责去办仍然是个烫手的山芋,最后又不得不落在我的头上。这些小事都足以见到当年物质的匮乏已经到了何等的状况。
其实经济上的计划经济弊端在当时并不引人注目,毕竟当年那不是头等大事,当年的头等大事是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挂帅,这种头等大事其实就是“整人”和“被整”的反复,这种反复从上而下一直到基层,我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的几年中,就目睹了从1972到1973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到1974年的批林批孔,然后1975年“以安定团结为纲”的整顿,最后是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每一次的反复本质上就是权力的分配和争夺,表现的是整人和被整。这种政治上的反反复复让人无暇去过问经济发展,所以到1966年国民经济到了行将崩溃的地歩。
将近30年愈演愈烈的政治运动,使人性不断的溃败,具体的表现是能够坚持自我的人越来越少,更多的人是在言不由衷的说假话做假事,我当年每年必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如此。那是项什么工作呢?那就是每年三四月份金牛区商业局要召开的全区商业工作会议,会议的第一天由局领导作去年工作总结和今年工作安排的报告,这份报告从工作分工的角度是由我起草的。我是怎么完成这份报告的呢?首先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有很大一个块头文字不少并且要摆在报告之首的是当年的政治运动,不管文字有多少这部分是很好办的,首先有各级党委的红头文件,再就是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面都有详细描述照抄下来就行了,当然得不痛不痒的结合一下实际。接着是去年工作总结,既然是商业工作会议当然是要讲经济状况了,不管当年的实际情况如何,让商业局的计划财务股把去年各种经济指标执行情况给我拟出一份详细情况,我总可以避实就虚避重就轻的找出一大堆有的是同比有的是环比的数据,来说明去年的工作状况也就是去年的经济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试想这样的工作中,哪里还有半点自我,我已经不是我,不过是报告中的一个标点符号而已。
如果一个社会发展到构成这个社会的成员们,或者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思维,或者即便有自己的思想和思维但仍然群体的习惯于说假话做假事,自己的所思所想或者是因为外部的原因不能讲,或者是因为自我的原因不想讲,讲出去的都是些言不由衷的套话假话,从宏观上看这个社会还会有希望吗?还能够向前发展吗?但当年的情况确实普遍如此,大家都每天嘴里说着自己心里边不想说的话,手里做着自己心里边不想做的事,但却正儿八经的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着,政治上有运动,经济上有计划,至于个人就在运动中运动,计划中计划吧。
这种人生应当是乏味的,但无聊和无奈之中也有朋友,当年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的那几年中,我就曾结交过两位朋友,一位是金牛区商业系统内部的,一位是金牛区商业系统外部的。内部的这个朋友叫曾长明,他其实是和我同批从蒲江县招工回来的知识青年,集中培训学习完毕后分配在比较偏远的三圣供销社工作,1972年金牛区商业局按区政府的要求办起了茶店子旅馆,主要的工作是接待金牛区各项会议,商业局让每个供销社推荐一名优秀员工到茶店子旅馆工作。曾长明的天性实际上是那种比较顽皮甚至比较调皮的职工,他肯定不会是优秀员工,但体制的弊病使三圣供销社的领导把他推荐给了局里边,本质上是甩掉一个难管的刺头员工,他于是到了在茶店子旅馆,先是从事楼层服务员工作,后来拜师学习了白案后就到食堂中去从事白案工作了。因为当年要组织各种会议我经常在茶店子旅馆,各种原因是我和他成了朋友。
我和他成为一批朋友外界其实一度很是惊奇,好像我们差距太大,当时外界始终认为我是商业局的局长秘书,是未来的局长接班人,而曾长明一介白案师傅,文化程度初一也不高,怎么会成为我的朋友呢?但事实是我确实和曾长明成了至交和朋友。使我和曾长明成为朋友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交流和交往中他最后明白并且认同了我是一个与世无争与世无求的人,他相信我当年那样引人注目的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实际上是一种暂时的权宜,而他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也是如此,用当时他自己的话来说人活着只要快乐就行,这种共同的人生观念使我们能够毫无隐瞒的畅所欲言。在我这一方面,与曾长明交为朋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假,在我的面前不装扮任何假象。
从表面上看曾长明似乎寡言少语甚至不善表达,他其实内心思维还是很丰富,因为我的原因他后来与当时金牛区商业局的一把手张局长也混得较熟,连张局长后来都说这个曾长明其实是有思想并且很会讲话的。我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的几年中,因为内内外外的很多原因,其实还是很郁闷的,甚至有的时候比较人为的压抑,应该说曾长明在这几年中作为我的朋友,在倾听我的心声排解我的纷扰方面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与曾长明的交往及结成朋友,说明一个人在社会上人世间展示自己真实的一面才是重要的,我与曾长明就是这样的,我们各自展现在对方面前的就是自己的本来面目,没有伪装没有乔装打扮,怎样想就怎样说怎样做,自然朋友的友谊基础就很坚实了。
(未完待续)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6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5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8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衣食住行(25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263)
-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前言) - 01/28/25
- 欧州旅游:中东欧(三) - 01/27/25
-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02) - 01/2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