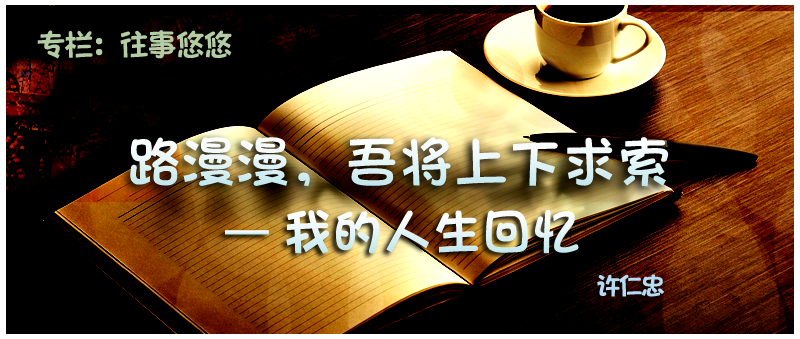
(续)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
当年认识和结交的一个金牛区商业局系统外的朋友是成都晚报的一位刘姓记者,认识这位记者的过程也很有趣,我当年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一天到位于庆云南街的成都晚报去办点事,那个事情本身不难,但因为涉及到一些内内外外的因素,我在成都晚报被踢皮球似的几个来回后,偶遇了这位刘姓记者,后来的交往知道他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不然当天他也不会来管我这个闲事了,这也许是一种缘分吧。他听我简单的说了几句我要办的事情,于是就像指点迷津似的直接把我带到了应该解决这个问题的地方,可能是因为有他陪同吧加之问题本身也不难,所以事情很快就办好了。在感谢他的时候我给他说了我工作的单位,没有想到巧就巧在他那两天正好接到编辑部的任务,要采访一遍似乎与我工作环境比较接近的新闻,于是简单的道谢和道别变成了我和他的交谈和沟通,最后的结果是约好让我在我的工作环境内陪同他第二天去进行采访,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就是十分简单和方便的了,能有这种机会对他进行直接的感谢我认为是太好了,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成了我在当年的一个工作机会,并且因为这个事情最终和这位刘姓记者成了朋友。
他要采访的题材是当时安排的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新闻,政府机关工业企业他都进行了采访并积累了相应的素材,虽然是作为点缀还是应该有点商业支持农业的内容,他正苦于在市区中去了几个商业部门似乎与农村都隔得较远,碰到我这个金牛区商业局也叫金牛区供销社的干部,这种事情就是小菜一碟了。第二天我与他约好在石羊供销社碰面,推荐和选择石羊供销社除了那里确实有很多支援农业生产的可供采访的题材外,我对石羊供销社与石羊公社比较熟是很重要的原因。我的人头熟确实在他的采访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了让新闻报道有一定的深度,他还要去采访一下大队生产队社员对供销社的反映,因为我曾被石羊公社借调去驻队,对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很熟,所以当天我直接把他带到了他想去的地方,很圆满的完成了他的采访。
他后来在完成这篇新闻稿的时候,本来是作为点缀的商业部门支援农业生产反而因为他采访的素材深度和广度都很好,于是这篇新闻稿里商业支援农业的内容反而喧宾夺主成了主要内容,当年各行各业支援农业是很重要很广泛的一个题材,他这篇新闻报道在报社中方方面面都得到了肯定和好评。因为我在金牛区商业局也是分工文字工作的,他看我有一些基础,便投桃报李让我参加了成都晚报当年举办的一个通讯员培训班,培训完之后我就成了成都晚报的通讯员,这对我的工作应该是一个特别好的支持和帮助,当年那个政治氛围下,能上党报进行宣传是很多单位梦寐以求的重大好事。事实上从那以后我就以成都晚报通讯员的名义投稿了,每次送去的新闻稿刊发的几率都比较高,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金牛区商业局以及下属的一些供销社各种新闻报道见诸成都晚报的数量明显增多,这让各方面对我的工作刮目相看当然也相应提高了我在单位中的地位。
因为有这些过程我和他的私交便逐渐密切起来了,交流中明显的感到他是一位心直口快眼睛中藏不住沙子的人,这样的人在当年特别是在宣传口是极少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当然他这种有点嫉恶如仇的天性会影响到他个人的一些生活的,认识他的时候他应该有40多岁了,居然没有婚配没有孩子,都是我认识他有一段时间之后他才有了自己的家庭后来增添了一个小宝宝。有了家庭和孩子之后,他日常生活上对物质的需求当然也会增加,在当年什么东西都凭票供应的情况下,我在金牛区商业局物资分配上的一些权力自然会对他有些帮助,所以我也逐渐的与他的家庭熟悉起来。工作上他一直对我的支持很大,甚至后来金牛区商业局要召开商业工作会议,我邀请他采访,他不仅来采访,并且两三天的驻在会上,这对我的工作无疑是很大的支持。
其实我与他后来相交甚深,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我们都是朋友相交坦然以本来面目相对,就象我跟我的同学陈大沞与同事曾长明相交的基础就是真诚一样,没有伪装没有假象更没有虚伪,他在报社我在商业局各自有些什么喜怒哀乐的事情,对方就是最好的发泄对象,不仅在工作上包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烦心事我们都能相互宽心和排解,比如他的家庭生活,比如当年我已经二十好几了仍然没有恋爱和女朋友,我们双方都毫无隐瞒的把内中的应该是比较隐密的情况毫无保留的让对方知晓,当然得到的回报那就是真正朋友的理解支持和帮助。
我与这位刘姓记者的友谊和工作上的相互支持一直维系到1978年我考入成都工学院读大学,因为我在四年的繁忙读书中结了婚并且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学习和生活的烦忙使我和他的联系逐渐减少,到我毕业分到四川财经学院任教后,也许是职业的差异吧,当然更多的是当年我确实方方面面都紧张,既要教学搞科研,家庭两个双胞胎儿子需要的费用也不少,忙碌中随着交往的日益减少我们的这种朋友关系也在淡薄,但对他在那几年与我的方方面面的交往还是使人难以忘怀的。
1976年是沉闷得使人窒息的一年,这种沉闷也许昭示着有些事情已经走到头了,情况要发生变化了。在这之前的1965年4月1日,一直想取代当年在“以安定团结为纲”下进行国民经济整顿的邓小平的张春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文化大革命将近十年的浩刼,从理论上推向了一个高峰,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种继续革命是持久的,“每隔七八年就要来一次”。其实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几年,方方面面的形势已经很严峻了,多年的政治上没完没了的运动折腾,已经使济状况十分恶劣,整个国民经济面临着崩溃的局面,主要表现在各种主副食品和轻工业产品的匮乏,凭票供应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商业部门经常在为兑现和保证这些票证供应上已经尽显疲态。
进入1976年,先是周恩来总理1月9日的逝世,为纪奠周总理的逝世爆发了“四·五”天安门运动,最终引发了二次出山的邓小平先生被全面解职并再次落难。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后,各地的地震传闻不断,四川成都也在疯传西部有大地震,让人没有想到的死了数十万人的地震发生在华北平原的唐山,后来四川也发生了传闻和预料中的地震。在人们人心惶惶的时候,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离开了中国人民,全国人民陷入悲痛之中,10月6日一直兴风作浪作恶多端的“四人帮”被粉碎,天终于要亮了,黑暗即将过去。
将近三十年的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各种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以及各式各样的说教,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四人帮”抓起来就能解决的。人们在经历了粉碎四人帮两三个月的欣喜之后,发现大的趋势大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根本性的变化,仍然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并且因为毛主席已经逝世了,就出现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先生曾经很风趣的说,“如果这两个凡是要坚持,我就不能出来工作了”,还好在邓先生复出的事情上没有贯彻“两个凡是”,邓先生第三次出来工作了,并且自告奋勇的主抓科技与教育,这是我们77、78级的福音。1977年年中传来了要尽快恢复高考的消息,消息很快成为事实,决定在1977年11月恢复中断了十多年的高考,这是我们老三届的福音,也是全国高中生或者是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人的福音,消息传来开始我就全身心的投入了报考大学的准备工作,在这之中也结识了不少“考友”。
当年的大学报考资格幅度很宽,没有年龄的要求,具有高中学历或者同等学历的人均可报考,事实上除了我们老三届是主体之外,正在乡下当知青的74、75、76高中毕业生,以及当年在校的从高一到高三的学生均可报考,于是就有了这种情况出现:考场中事实上今后进入大学后既有三十一、二岁的老三届高66级学生,也有只有十五六岁的在校高中生,大家同堂应试,同窗读书,好一派孜孜求学的美好景象。
(未完待续)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9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9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9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9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9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9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2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9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4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92)
-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前言) - 01/28/25
- 欧州旅游:中东欧(三) - 01/27/25
-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02) - 01/2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