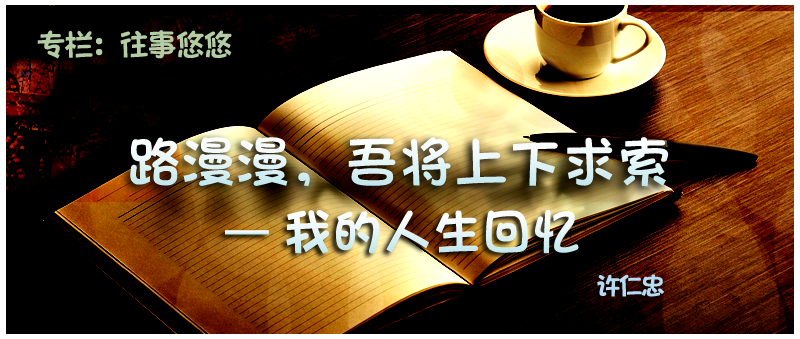
(续)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
其实在我与厐皓教授的交往中,他就是个学者,与他交流中当然也难免会涉及到一些行政事务他往往比较平淡,但话题只要一进入数量经济这个学术领域,他的精神就来了,比如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可能在他的心目中我是学数学的也许对模型中的某些地方会有自己比较好的见解,所以我和他曾多次谈到计量经济模型,其实我对计量经济模型了解是不深入的,我更多的是用模糊数学方法处理经济管理问题。个人认为他走上从政的道路也许对他不是最好的吧,当年他和那个最后身陷囹圄的前副省长李达昌一起因为在科研上成果突出,当年又很强调提拔优秀知识分子,两人于是被选中提干,李大昌去了校外做厅级干部最后官至四川省副省长,而他留在校内做了副校长,据说最后也有意请他做正校长,在征求他意见时他委婉的推脱了,但我认为以他的气质和喜好而论,他也许更适合做教授做学者做教学做研究吧。
在学术上与他产生共鸣之处是1988年我到科研处担任了处级干部之后,应该说当年我与他一起做成了一桩对西南财经大学教师有所补益的一桩事,那就是让西南财经大学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落在了实处。西南财经大学学术专著出版基金是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提供的,当年出版社还没有和学校完全分开脱钩,学校决定了出版社每年利润的相当份额要资助教师出版学术专著,当年庞浩副校长分管科研,这个虽然原则定了但还要有具体的操作办法和执行程序,这个事最终落到科研处和我的头上了,我们当年制定了一个很好的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教师出版学术专著的办法,效果还不错。在制定办法和执行的过程中,我感觉到庞皓教授他对这种事情的关注比对那些纯粹的行政事务要强烈的多,而且我感觉到他自己是身心投入的,所以我说他应该是一个学者而不是校长。
当然要说我与庞先生只有学问之交而没有人性情谊之交也是不妥的,做学问之人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我和庞浩教授在私交上还是颇有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当年我曾经组织全国财经院校数学教师到成都召开过好几次会议,有学术研究的也有教材编辑的,每次会议的闭幕仪式都要请庞校长来参加,应该说一个学校的校长还是很忙的,像我们这种专业面很狭窄的会议,去请校领导参加还是比较困难的,应该是基于个人方方面面的一些情谊吧,他每次都抽出时间参加了我们这边会议的闭幕式,给予了我工作上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当然,当年我要从西南财经大学科研处辞掉处级干部的职务时,党委还是很审慎的,基于我和他的私交甚好,党委还专门委托他与我进行了深度的沟通和交流。但不管怎样,以我在交往中对他的观察和了解,他似乎还是做一个教授做一个学者更合适些,而且以我的感受做一名学者也许也是他自己的意愿和期望吧。
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呼声中,八十年代过去了,但改革的步伐和效果好像都不大,严格的说除了因为“承包”调动了生产者劳动者的积极性,使得一度十分匮乏的主副食品和轻工业品的供应迅速好转,国人甩掉了票证,只要有钱就能买到自己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但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进展并不大,那个计划经济的桎梏价格,在整个80年代仍然是由计划制定而没有由市场所取代,所以国人的生活状况改善了,精神面貌精神需求也得到很大的满足,但改革却还没有真正的迈开步子,无论是国家还是老百姓都还谈不上富裕起来了,憧憬中的市场经济机制离建立好像还很遥远,而其中的关键是理顺价格,要让价格脱离计划,价格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进入九十年代特别是1992年小平南巡后,市场好象得到突然的激发一样很活跃起来,这之中金融逐步进入市场机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取得了信贷支持的中小企业在市场中有点自由游弋的味道了,在这种背景下价格被逐渐的放开,虽然引发了1993年开始的通货膨胀,但在人民银行采取的“保值储蓄”措施下,价格的放开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至少没有形成八十年代那种抢购风潮,经济体制改革迈开了比较大的步伐。
价格放开之后一个很现实的紧迫问题就是让企业如何走入市场融入市场,市场经济的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乃至生产资金的支持都是由市场来调控的,以前一切按计划执行的老路终止了,企业的生存与市场息息相关,有了市场你就有了一切。应该说九十年代在一定的阵痛和代价之下,这个问题虽然难度很大但最终还是以各种方式得到了解决,当然代价也是惨烈的,他让一代人做了史无前例的“下岗工人”,而这一代人恰好就是我们从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出生的人,我们无数次的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与牺牲。但不管怎样市场的机制总算初步建立起来了,经济活动不再是计划支配而是市场在调节了。
我作为体制内事业单位的高等学校教师,这种由计划到市场的变革对我影响本身不大,加之一些偶然的机会又让我顺应市场的活跃投入了市场经济,当年在杨成纲校友指点下学习到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市场经济学的一些知识在这个时候起到了他该有的作用,所以总体状况还是不错的。由于我比较谨慎的一直保留了体制内西南财经大学教师的身份,只是在完成了教师工作任务后才在市场经济中游弋一下,于是我成了某些校友喻为的“既享受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又享受了资本主义优越性”的状况,当然我个人对自己的这种选择是十分满意的。
一个在八十年代始终困难重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市场机制建立问题,在九十年代就这样被迎刃而决了,个人认为这绝不是一种偶然,虽然两个年代有各自很强烈的政治经济背景,但人心所望人心所至应该是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经过八十年代那种成效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磨难,国人逐渐认识到没有改革是没有出路的,计划经济的老路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只有齐心合力的建立起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大家才能逐步富裕起来,共识使国人趁着九十年代良好的政治经济形势,克服各种各样事实上也存在着的困难,让市场经济的模式得以初步建立,尽管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
除了在改革上来了一大步外,九十年代在开放上势头也不错,应该说九十年代初甚至包括整个九十年代,开放所引进的外商投资其实主要是以港澳台同胞为主的,第一批进入中国大陆投资的是台湾香港澳门的中国人,虽然投资的规模不是很大,但给国人带来了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概念,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当时的汽车牌照与普通国人的汽车牌照是明显不同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标志问题,它事实上在向国人宣告境外投资者来国内投资了,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使港澳台同胞很快就理解和相信了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他们毫不犹豫的迈出了向大陆投资的第一步。
整个九十年代我过的是相当于愉悦的,这其实也是工作和生活紧张所致,充实的生活节奏让人身心愉快,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其实问题的另一方面也是很严峻的,就是当年我面临着好几桩需要做出抉择的事。首先是体制内外的问题,也就是说我是要选择全身投入市场经济中,还是仅仅是摸着石头过河试试而已进而浅尝辄止,当时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中我面临着比较好的发展机遇,具体的说就是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支持,当年所面临的良好局面足以让我把事业做大做强,无论在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上面,还是在要取得资金支持的金融人士的关系上面,我都有很多优越的条件,给人的感觉应该是全身心的投入市场经济为好,但事实上我没有脱离体制内,在工作是很紧张的情况下我仍然坚持了完成西南财经大学教师的工作任务,从而保持住了体制内事业单位高校教师的身份,后来的事情发展和结果说明当年这个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再就是工作繁忙和子女教育的关系抉策问题,当年在市场经济游弋吋,也是我的两个儿子学业最为关键的中学阶段,在这个问题上我似乎是十分的清醒明白,始终都是把子女教育摆在第一位的,没有因为既要在市场经济中拼搏又要保持自己的公职人员身份所带来的工作繁忙便把子女教育疏忽了,事实上在他们中学的几年中,我和我的夫人身体力行的操刀上阵为他们学习数学和英语进行超前教育,应该说最后的效果是良好的,儿子们在1999年一个考上了北京大学,另一个考上了北京航天航空大学,这为他们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也为自己这种明智的选择感到自慰和高兴。
(未完待续)
许仁忠: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144)
许仁忠: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143)
许仁忠: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142)
许仁忠: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141)
许仁忠: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140)
许仁忠:19世纪的欧洲科学技术与第二次工业革命 (139)
许仁忠:19世纪的欧洲科学技术与第二次工业革命 (137)
许仁忠:19世纪的欧洲科学技术与第二次工业革命(13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3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3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3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3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2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2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2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25)
-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前言) - 01/28/25
- 欧州旅游:中东欧(三) - 01/27/25
-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02) - 01/2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