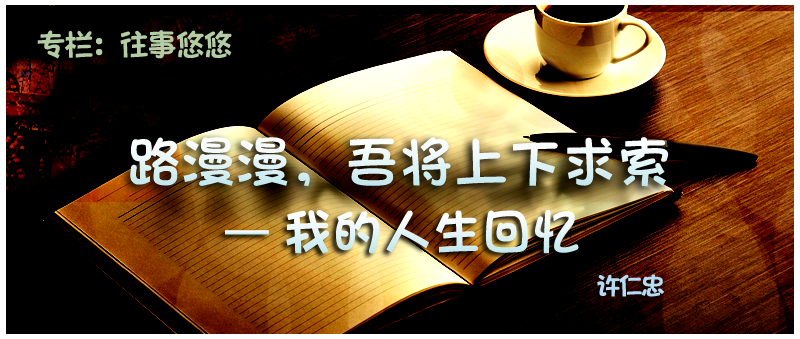
(续)第十七篇 赤橙黄绿青蓝紫——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
接下来想说说我的“文字”,这也是有点自我飘扬的内容,前面已经说了不少自我表扬的“琐事”让老年人很高兴,既然能高兴那就多说点吧,老年人还是要自己去找一些能让自己高兴的乐子。关于一个人的文字,有一句话说的是“文如其人”,说的是一个人的文字是如象这个人一样,好像更多的说的是一个人撰写的文字就像这个人一样,这里说的是撰写文字的过程,我把它再加上四个字“文似其人”,想要强调的是一个人的文字特别是它的风格是与这个人很相似的,更多要说的是一个人已经形成的文字与他其实是很相似的,这里说的是所写成文字的结果,当然这两句话说的内容是很接近容易混淆的,不过仔细体会它还是有各自的侧重。
对文字撰写的喜爱可以追溯到少年,当年有一点文化的父亲或多或少起了一些作用,我记得引起老师和同学们关注和表扬的大概是小学三年级我写的一篇作文。那篇老师的命题作文的标题已经记不起来了,内容是对在成都市人民体育场内国庆节放熖花的记叙,当年放熖花不像后来更不像现在那样从地面射向天空起爆,而是把各种类型的鞭炮之类的熖花捆绑在一个架子上进行燃放,这个架子被称为“熖花架”,那个时候的人们特别是孩子们都用通俗的成都话把看燃放熖花说去看“烟火架”。
解放初期的最早的烟火架是在皇城坝燃放的,捆绑烟花的架子就架在皇城坝上老皇城的正大门前,市民都拥挤在皇城坝上看放熖花。1953年占地面积90000m²的成都人民体育场建成,它有观众席位25000个,场内有400米跑道10条及足球场一个,是成都市主要体育活动中心。1953年的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有近3万人参加各地选拔,1200多名选手到大会参赛,观众达48万人次。成都市人民体育场建成后,1954年国庆节燃放烟花的“烟火架”就由皇城垻迁移到了这里,“烟火架”是架在足球场中的,观看的市民都坐在看台上观看。
我那篇作文就是描述和记叙的当年燃放熖花的情况,绝大多数同学在完成老师的命题作文时,都把重点放在熖花的燃放上,我的得到老师肯定和表扬的那篇作文,写作的重点不是熖花的燃放,而是对熖花燃放前熙熙攘攘的人群在等待焰火燃放时的众生莹莹像上,主要是描述和记叙了观看熖花的人们熙熙攘攘拥拥挤挤的情况,特别是人们在等待燃放熖花的时候那种欢喜但又略有焦灼的心情。老师把我这篇作文在向全班同学讲读时,重点表扬了我对熖花燃放前先是人声鼎沸,待第一炮熖花燃爆时全场瞬间安静下来的那段文字,我现在还依稀记得当时用了很长一段的排比局来描述看台上人们的熙熙攘攘声,诸如“男人的吼喊声、女人的尖叫声、小孩的哭闹声、大小的呵斥声”等等,然后是听到砰的一声后全场迅疾的安静,人们很快就进入了观看熖花的角色。作文被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阅读宣讲,这种在幼年时候就得到的殊荣应该说是开启了我对文字撰写的喜好之心。
对自己文字能力有所提高的是在成都二十九中读初中时承担的一份编黑板报的社会工作,当然这份工作是由好友洪时明兄与我合作承担的,我负责每期黑板报的组稿和编辑工作。最大的锻炼是要独立构思出每一期黑板报的中心思想,当然也包括为展示这一中心思想的一篇核心文章,正是这份社会工作让我明白了如何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思维,更是让我享受到了能用文字恰当的得体的表达自己思想的乐趣,当自己所想所思成为文字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一种满意和自得油然而生。做这份工作时当年和洪兄为了赶急有时就迫不由己由我口述文章洪兄抄写,因为不是用粉笔在写而是用毛笔彩粉在写,所以我口述的文章应尽量不出需要修改的文字错误,这一点客观上对我的文字表达是一个很大的锻炼。
其实更大的锻炼是黑板报的编辑和组稿工作。每一期黑板报都得有一个中心思想,当年虽然是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但比较好的是校方没有任何人向我们提出要宣传阶级和阶级斗争。其实真要宣传“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心思想和主题反而容易确定了,因为没有这种政治色彩上的东西,使我在确定每期的主题和中心思想的时候还是要下点心思和功夫的,当时首先着眼于功课学习上,为此我和很多科任老师都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听取他们的指导和意见。再有就是关于音体美文艺方面的一些内容,在这些方面我很弱,但洪兄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作用,他时不时的点拨和建议也会让我确定这方面的一些宣传主题和中心内容,当然也会有一些日常生活方面的常识呀甚至注意事项呀成为主题和中心思想。
后来读高中了读大学了工作了,回过头来看这份确定每期黑板报主题和中心思想的工作也许是我漫漫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起步点,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每周都有这么一项事情需要去思维去思考,最终由自己去决定一个东西,这样的锻炼机会事实上是不多的,至少对多数的初中学生来讲不容易得到这样的锻炼机会。后来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自我总结我对每一份工作都是安排的井井有序,特别是对工作的轻重缓急总是考虑的比较仔细和到家,这恐怕和少年时代的这种锻炼分不开的。
每期黑板报确定了主题和中心思想后,便是组织稿件的工作,说一句当时工作的实际情况的心里话,就是向同学们去组织稿件困难之大还不如我自己去写。首先当年是处于大家饭都不大吃得饱的年代,很多同学对于读书都感到没有多大兴趣,谁还愿意来写这种黑板报稿件。再就是对于每期的主题和中心内容,我得要去物色和选择比较适合写相应文章的同学,说一句不得体的夸张话,就有点像导演去找演员一样,找到了那位同学除了苦口婆心希望他能撰写稿件外,还得像导演说戏一样给他讲明这期板报的主题和中心思想,他这篇压轴的文章怎样写写成怎样对我们黑板报很重要,有时甚至想干脆像老师的命题作文一样给他出个题目让他写,但客观的现实显然这样是很不好的,还得让黑板报文章的作者们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当然事实上和客观上当年我自己捉刀撰写的文章也不少,但这更多的是无奈之举。所以更多的时候都在想还不如我自己动笔写了还省事些,但这显然是不行的,还得刻意的尽量的找一些各个班的同学来写稿。
这项组织稿件的工作对我的锻炼也是很大的,让我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受益匪浅。在我后来几十年的工作中,无论是上世纪70年代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还是80年代在西南财经大学工作特别是承担组建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和组织全国高校一大批老师编写数学教材,以及90年代下海经商既要自己公司经营还要帮助很多朋友管理公司,特别是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我担任了几个民办高校的院长工作,所有我的工作所涉及到的人,包括领导和同事、工作的对象和工作的团队,都认为我这个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沟通,很多事情特别是有些看似很难的工作,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大家似乎都明白了事情的由来和发展,特别是很明白我的思维和思考,使得各项工作都得到了很好的完成。我想这应该是尚是少年的我在当年就得到了这种与同学作深度沟通交流的机会和锻炼的结果吧。
我所撰写的文字在风格上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逻辑性比较强,似乎也有一点追求哲理性的倾向,这恐怕与我从初中时就开始在数学等理科课程上表现出来的喜好有关。在初中阶段我对于数学物理化学甚至包括生物这些理科课程,我逐渐表现出一种挚爱与喜好,尽管对语文课程还是很喜欢,特别是考入成都七中后,这种对数学的偏爱就更为明显。数学严密的逻辑思维不知怎的有点逐渐进入了我的文章风格之中。记得当年由我执笔所写出的成都七中第一篇把矛头指向当权派的大字报,有用心的同学在读了之后与我交流的时候半开玩笑的说到,许胖子你这篇大字写得就象在做一道大的数学题,在提出论点之后尽力的在用各种证据一层一层的在推理,希望用论据去证明结论的合理性。这句话确实一语中的,当年我在与好友刘仁清交流了大字报的主题和中心内容后,文章的架构包括论点与论据一直在我头脑中盘旋,我始终在寻求论点和论据的和谐与统一,重点想要说明的就是“是什么”与“为什么”,所以当晚一气呵成的这篇大字报确实是很致力于逻辑性的。
(未完待续)
我的更多文章: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前言)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0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2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70)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八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七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六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五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四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三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二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一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十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九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八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第七篇)
-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前言) - 01/28/25
- 欧州旅游:中东欧(三) - 01/27/25
-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02) - 01/2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