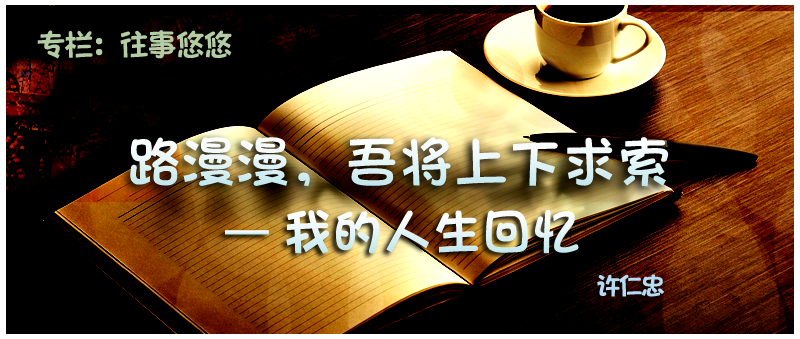
(续)第十四篇 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我的“城南纪事”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第一个是十年中度过的,应该讲总体是很愉悦和自由的,特别是这个十年中1956年前的那些年,除了儿时晃荡在皇城坝和金河所带来的惬意,更多的是在与罗家的交往中罗家三位小哥哥小姐姐带我认识的世界,这个世界既包括具体的,比如他们带我认识和了解了大学,使我在这一辈子与大学结下的不解之缘中,从年幼的时候便开始知晓了大学为何物。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与罗家小哥哥小姐姐们交往的过程中,他们让我对抽象的世界有了一个朦胧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人皆平等且需自由,当年无论从贫富差距上来讲还是从知识教养上来讲,罗家小哥哥小姐姐与我的差距都很大,但他们那种真诚与热情给我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对于人来讲差距不是主要的,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就是我与罗家小哥哥小姐姐那种平等和相互尊重,以及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自由。到现在迈过古稀之年来回忆这一辈子所行所为的时候,才发现从儿时就开始萌发的人皆平等且需自由的观念,其实支配了我的一生。
童年时代的欢悦还与二十世纪50年代的人际关系有关,尽管新中国建立之后,也有了各式各样的运动,但在1957年反右之前的各类运动,整人也就是把人作为斗争对象还不明显,各类运动多是以教育为主,就是教育你要改造思想,跟上社会主义的步伐。即便在1957年出现了那种疾风暴雨般的反右斗争运动,有几十万人其中特别是知识分子被作为斗争的对象而被整,但来得快去得也快半年多的时间一晃而过,进入狂热的1958年后,便有了热烈而激动人心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高产卫星超英赶美大炼钢铁让大家都处于一种亢奋之中,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由于不明事理自然会有一种虽然是盲目的但却真正是来自内心的一种欢愉,直到1960年末出现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时,人们才从兴奋中冷静下来,欢愉也就戛然而止了。
尽管总体是愉悦的,但二十世纪50年代后半叶特别是最后的两三年也萌发了一些人生阴影,少年的我观察人生虽然并不深刻,但也感触到了一些,比如从57年反右后,人们似乎不大爱讲话了,准确的说是人们不大爱讲真话了,五七年反右斗争那场运动告诉了人们“祸从口出”,因为当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在反右斗争拉开帷幕之前,积极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讲了很多似乎当时不应该讲的话,被当做了斗争的对象成了右派分子,好像一切都是因为爱讲话引发的,所以告诫了后人少讲话不要讲真话。
我的家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亲因为爱讲话被划为了右倾思想被下放劳动,母亲因为参加了工作就认为自己有组织有依靠了,对家庭不是很关心了,这些变化使我的家庭有些支零破碎的状况,人不多就五个人,但却分在四处少有团聚。好在我于1958年9月转学到了望江楼小学,并搬到了四川大学员工十四宿舍住家,新的学校中结识了一批家在四川大学成都工学院的同学,其中有不少是这些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子女,与他们在一起方方面面都有所升华。特别是搬到四川大学居住后,才真正近距离的接触和了解了大学,这种接触和了解使我在后来的一辈子中都与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50年代后半叶特别是那场反右斗争运动带给国人的心理阴暗面其实是很严重的,它很深很深的影响了国人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好像都带起了一个面罩不大容易看得清楚对方了。在我的少年心理中,最使人不解和遗憾的是,自从公私合营开始之后,罗家包括三位小哥哥小姐姐与我们的关系就开始疏远起来,其实主要是他们在躲着我们,似乎有很多难言之隐。再就是后来搬到四川大学居住后,见到了不少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他们其实原来是很被人尊敬的专家学者,一夜之间就成为了人民公敌般的狗屎堆,而更使人遗憾的是似乎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坏人,其中有不少人在当年那个政治环境下应该是发自内心的认为就是这样。
让人百感交集的50年代走完后,迎来的是吃不饱肚子的三年困难时期。尽管是饥肠轱辘的三年,毕竟是生活在城市,中学生定量偏高的商品粮保障,加上相当能干的母亲时不时能弄点回来的“油大”,辅以瓜菜包括南瓜花的充填,肚子还能勉强填饱。而这三年其他方面相对就比较好了,在成都二十九中读初中的三年,学业优秀同时结识了一批也很优秀的同学,家里边也逐步恢复正常,父亲结束了在青白江成都钢铁厂的劳动改造,回到了成都在国营的贸易公司正常工作,母亲所在的消费合作社也成了国营的百货公司,更为重要的是母亲结束了“半边天”的奋斗,逐渐回归家庭。
在成都二十九中上初中的三年,三年中每年的六月一日,我都是在四川音乐学院度过的,是在那里观看一年一度的庆祝六一儿童节音乐会,可能算是一种工作表扬或者奖励吧,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学校团队干部彭老师都要给我一张去四川音乐学院听音乐的入场券,让我去享受少年时代的音乐乐趣。我这个人自己对音乐完全不行,既不会唱歌更不会玩乐器,但对欣赏音乐却情有独钟,也许是儿时受罗家小姐姐带我去四川音乐学院看大学生练琴的影响,所以对音乐特别喜欢,当然是喜欢听音乐。其实说到音乐包括歌曲,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大环境中,特别的表现出了它的时代的烙印,每个特殊的年代都有好像能特别表现它的音乐或者歌曲,现在退休了年老了,每当听到那些音乐,脑际中就会出现当年不同年代的情景,甚至会浮想联翩的回忆起当年的彼人彼事。
困难年代的三年是人际关系很平静的三年,尽管其间也有这样那样的运动,估计大家都是机场轱辘的,也提不起精神来整人,大家全力以赴的是尽量填饱肚子。当年稍有点条件的家庭,都会种瓜种菜,其中种南瓜是最普遍的,相比其他蔬菜瓜果,好像南瓜是最为实在的,对于充填肚子的功效最为明显,因为种南瓜的人多,而且不太择地方,任何一个边角上都可以,这样当年我从成都三官堂涉水过了锦江在穿过四川大学到成都二十九中时,沿途有遍地的南瓜,开花结果季节我会沿路采摘雄的南瓜花,回家把它撕碎后洗干净,放点油盐炒一下加水煮成汤,再加入面粉揉成的面块,一个南瓜烩面便做成了,不仅充饥那味道嘛就不摆了。
困难的三年似乎过得也很快,很快的进入了1963年,因为一些政策的纠偏,比如在七千人大会后对农村农民也就是人民公社社员自留地的栽种和家庭副业的管辖有所放松,集市贸易也允许交易,各种各样的主付食品开始逐渐多了起来,仅管很贵但只要有钱还是能买到一些了,大家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我也在那一年的9月考入了成都七中读高中。
进入成都七中读高中对我来讲也就是告别了少年进入了青年,读高中的三年中感觉在思想上有很多变化,而其中最明显的是幼年和少年时代所萌生的那种人皆平等且需自由的思想有所发展和发挥,具体表现为既不想被人管,也不想去管别人,更不希望人们之间有更多的相互约束,期望着大家都有一种平等自由的生活环境。我的这种希望自由自在不被约束想法,在成都七中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得到了支持乃至纵容,因为各科的学习成绩比较优秀,所以各科的先生们对我的管束也就是具体的学习要求不多,更多的是一些比较高层次的教诲主要是思维的指导,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活中我有一种天马行空的感觉,实际上是达到了一种自我自由的境界,这对于我在后来几十年中做出很多重要的人生选择十分重要,所以确实要很感谢当年那些科任老师们。
高中的三年也是1963年到1966年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刼的酝酿期,在这三年中是逐步受到了一种左的思潮的教育与熏陶。从1963年底开始明确的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后,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被教育中,国人的思想被极大的教化和驯服,我自然也毫不例外的身在其中,具体的表现是思维越来越偏激左倾,凡事都不由自主的朝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方向上去想,所以当疾风暴雨的文化大革命到来时,便毫不犹豫的带着满腔的左倾思潮投入了进去。
(未完待续)
我的更多文章:
许仁忠: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144)
许仁忠: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143)
许仁忠: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142)
许仁忠: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141)
许仁忠: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140)
许仁忠:19世纪的欧洲科学技术与第二次工业革命 (139)
许仁忠:19世纪的欧洲科学技术与第二次工业革命 (137)
许仁忠:19世纪的欧洲科学技术与第二次工业革命(13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3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3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3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3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2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2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2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25)
-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前言) - 01/28/25
- 欧州旅游:中东欧(三) - 01/27/25
-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02) - 01/26/25
On 01/24/24 @ 1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