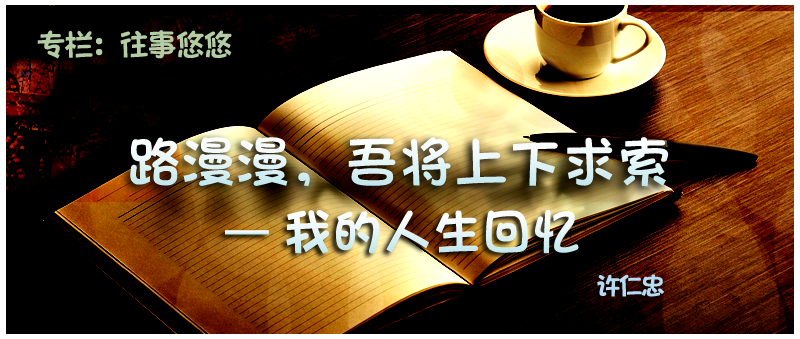
(续) 第七篇 欢乐与成功同在,遗憾与教训同行 —— 我工作与生活中的“得失”
所谓知新的事,是我从2006年开始接手了西南财经大学通识教育改革中的自然科学系列课程。2006年西南财经大学启动了一个有相当深度的通识课程教学改革,为了保证这个通识课程教学改革顺利进行,学校成立了一个通识教育学院,2006年9月入校的新生,第1年也就是大一的学习和生活都在这个通识教育学院进行,一年之后也就是大二的时候才按照专业进入到各自报考和录取的专业学院。这个改革是很成功的,从2006年开始,一直到至今都是如此,已坚持了十余年。
当然通识教育课程的改革的主角还是课程,当时校方设计了八大系列的课程,其中的一个系列就是自然科学系列,基于很多原因,既包括学校中其他的理工科老师不愿意去讲授这类课程的客观原因,也包括我个人的兴趣爱好及天性的主观原因,使我成了自然科学通识教育课程的主角,事实上我成为了后来开出的《科学技术史》与《大学物理》这两门自然科学课的课程负责人。
在研究通识教育自然科学系列课程的时候,开设《科学技术史》意见是很一致的,各方面都认为这是一门对西财学生了解自然科学很好的一门课程。而且开设《大学物理》课程,就比较费周折了。提出要开设这门课程的是当时西财经济学院的一位颇有声望的先生,他是在参加一次全国的经济学年会中接触到了并且接受了当时普遍认为物理学与经济学有一种相生相促的学术观点。尽管在讨论中有所疑虑,但我这个课程负责人最后还是表态试试再说吧,我当时的想法是觉得让经济管理的学生了解点物理学知识还是不错的。
这二门课程确定下来的时候已经是2006年五六月份,9月份新生入校就要开课,首先要解决的是教材和教师。《科学技术史》还比较顺利,聘请到了四川大学和省社科院三位先生,加上校内的三位老师,组成了一个课程小组,也选定了教材。《大学物理》就比较麻烦了,教师实在是找不到,最后只能由我与学院的另一位老师承担,那这位老师,也是我做了很多工作之后才应承下来的,教材最后也在众多大学物理教材中选择了一本比较通俗易懂易于经管类学生阅读的。
《科学技术史》确定是全学校所有学生的必修课,因为毕竟有6位教师讲授,把学生分成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两批分别讲授,也能基本满足师资需求了。《大学物理》是确定开在第一学期的选修课,没有想到的是入学之后的学生选修这门课的同学还比较多,而我们只有两位老师,编班时只好编成300人左右的大班,安排在学校最大的阶梯教室中授课。
讲授《科学技术史》与我个人知识和能力的提升是相互益彰的,一方面我的理科背景对讲授这门课程起到恰如其份的好处,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发展的脉搏,它的哲理它的起因它的史实无疑对我这个理科教师起着知识的积极的良好补充。
前者比如在讲授几何发展史中,从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中的第5公设,到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再到球面几何及至黎曼几何,熟悉相关数学知识的我,应当是把近两千年来几何发展的历史脉搏梳理和讲授得让学生引人入胜的。又如在讲授微积分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几乎是同时诞生的史实时,应当说我对数学和物理知识的极致的熟悉使课程的讲授学生和我都十分进入角色。
后者比如使我从对古代科学技术的了解有了更深的认识,到对古希腊古罗马科学技术的登峰造极,特别是包罗万象的哲学学派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和促进的有了更新的体验。特别是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结束后,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起始于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及葡萄牙西班牙的环球航海航行,得以使最先进的近代科学技术何以诞生在欧洲有了认识和理解的提升。
《大学物理》这门课程上得比较尴尬甚至可以说是狼狈。因为是确定在新生入校后的第一学期开课,很快就进入到了力学中的运动学和动力学课程,这时同学们数学上还没有学到导数,更没有学到积分,所以在讲授上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和矛盾,不能用高等数学去定义速度和加速度,使得课程讲授得特别的难受。
更为麻烦的是同学们的感受,没有高等数学的物理学,怎么能叫大学物理呢?本质上就是中学物理嘛!于是同学们的不满意油然而生。当然后来几届我都采取了在讲授速度和加速度前给学生补充导数的知识,这对提升教学层次和质量多少提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本身这门课的总学时就很少,这无疑又要影响到其他物理学知识的讲授。这门课就是在这种尴尬和狼狈中讲授了三、四届后无忌而终。
在我临近退休前接受和讲授的这两门课,对我个人来讲无论哪一方面来讲我都是感到很满意很充实很自知的,它不仅丰富了我的教学生涯,同时也满足了我历来就富有的挑战精神的欲望,而个人在这两门课讲授过程中无疑是愉悦和兴奋的,这确实是我在西南财经大学退休前一段使人可以回忆的愉快生活。
(未完待续)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9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9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9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9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9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9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2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9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4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7)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6)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4)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9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3)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2)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1)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0)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75)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79)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78)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77)
-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前言) - 01/28/25
- 欧州旅游:中东欧(三) - 01/27/25
- 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02) - 01/26/25

